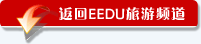冬天的夜晚,我悄悄守在天坛公园栖息着长耳鸮的树下。一只成年的长耳鸮站在天坛神厨的檐角,仿佛和屋角的石雕小兽一样成为夜空中凝望天空的雕塑。夜晚很寒冷,四周只有单调的风声,使得黑暗之中的古老院落显得更加阴冷幽暗。不经意间,几只老鼠细弱的叫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在这细弱的叫声之中,刚才雕塑一般的长耳鸮开始不断地转动头颈,好像是在侧耳倾听来自老鼠的微小声音——这个时候的长耳鸮的“倾听”是真正的又“倾”又“听”——它不断调整自己头部的方向,仔细比较着左耳和右耳声音的微小差别,以此确定猎物的位置。一边倾听,我的长耳鸮一边开始调整着身体的方向,姿态也有了细微的变化。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它可能要捕食了!还来不及按下手中相机的快门,它就猛然从檐角腾起,直直地向上空猛冲,然后一个转身扑击!黑暗之中传来一声尖锐刺耳的叫声,那是褐家鼠临死之前惊恐的哀鸣。整个捕食的过程只是转瞬的几秒钟,却看得我瞠目结舌。几分钟之后,借助头灯微弱的光,我看到长耳鸮叼着刚刚捕到的猎物停在一株粗壮柏树的断枝前,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每年的深秋这些长耳鸮都会回到我们的城市,它们有时候会在龙潭湖公园游荡,有时候会蹲在永定门的屋檐一角俯瞰南二环车来车往,有时候会突然出现在天桥的剧场之上;国子监的长耳鸮曾经短暂活动在和平里社区,也曾经被观察到在小街桥上空盘旋最后飞到雍和宫之中。
鸟类迁徙的必经之路
长耳鸮并不是唯一短暂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鸟类。红胁兰尾鸲、红喉姬鹟这些迁徙的鸟在每个春季和秋季像一阵风一样出现在北京,然后又像一阵风一样离去。它们是迁徙过程中的过路鸟,选择在北京作短暂的停留和休息。像它们一样在北京过路的鸟类有超过二百种。
在北五环的肖家河桥向北,每年的四月和九月登上百望山山顶,几百只几百只的灰脸狂鹰从头顶呼啸而过;在南三环靠近公主坟立交桥往东,杨树开杨花的季节也是太平鸟成群出现在玉渊潭公园的季节;在四环的西北拐角,2010年的3月间,几百只小天鹅在颐和园十七孔桥和佛香阁之间的宽阔水面上歌唱追逐,童话中的常常出现的知更鸟在人身边跳跃。
五年的时间,从什刹海到国贸,从圆明园到长安街,我和我的朋友在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之中拍摄了超过270种野生鸟类,十多种陆生脊椎动物,以及近百种昆虫和两栖爬行动物。实际上整个北京都是动物重要的通道。北京的地势西高东低,西北面是连绵的太行山和燕山余脉,东南面则是一望平川的平原低地。这样复杂的生境给各种各样的动物提供了多样化的栖息地选择和食物选择,而山口交汇抬升的气流也让迁徙途中的鸟类可以在长距离飞行之中节省体力。最近的几十年,伴随着高速的城市化,北京城市之中自然的绿地体系逐渐减少和破碎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中残留的绿地和公园构成了相对连贯的次生林-湿地系统,在今天整个北京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