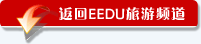明朝大兵赶走当地居民,乡村城堡上演“男耕女织”
在这个有着城堡意义和形象的村庄,大约在六百年前后,一群姓罗、姓杨、姓李、姓飞、姓海、姓王的明朝大兵,随沐英从南京出发,到了云南通海,被分配到杞麓湖南岸,建起了6个军营形象的村庄:上罗家营、下罗家营、杨李家营、飞家营、海家营、王家营。这是他们用武力赶走当地居民的结果。当然失败的当地居民也不会让他们安宁,报复和偷袭是经常发生的事。
在森严的兵营里,大兵们把抢来的姑娘,全弄成了一个个小脚伶仃的女人。
小脚女人被大兵们常年供养着,像江南一带的大家闺秀,足不出户。偶有露面,那必定有大兵们的团团呵护。这些小脚女人倒也知足,她们为了感谢这些优秀的兵哥哥,便拼命为他们生孩子,并把所生的小女孩,按照男人的要求,全部裹成小脚娃娃。对此,兵哥哥们的眼睛极为挑剔。因此这里的缠足水平扶摇直上,缠足技艺和脚的小、尖、弯、香、软的标准,都与古都南京接近。
后来兵哥哥们无力供养小脚女人了,她们便学会种蚕养桑,用丝线织出平滑光亮的“通海缎”。小脚女人们也因为劳动的成功,心头掠过一阵阵得意的春风。但是苛捐杂税容不得“通海缎”的风光,小脚女人们不得不放弃种蚕养桑,回头跪在男人面前,求他们供衣给食。男人们不再把她们当做闺秀,而把她们视为奴仆,随意在她们身上发泄性欲,随意强迫她们劳作。
1910年滇越铁路的开通,给小脚女人送来了洋纱和染料。小脚女人又从田间回到家中,织出有名的“河西土布”。她们用梭子撞开一扇倾斜着的穿衣吃饭之门。
当时六一村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纺织城。证据之一就是县内仅有的两个土布交易市场,六一村是其中主要的一个。
可以想象,封建社会那种“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和抒情的画面,曾在六一村隆重上演了一二百年。
六一村最后的小脚舞蹈
缠足是有源头的,我们在冥冥中看到那个令人羞辱的源头:公元前11世纪商纣王的妃子妲己的畸形小脚;南朝齐国东昏侯的潘妃步步莲花的情景;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命令宫嫔用帛缠足的诏书;北宋熙宁、元丰年间,少数几个汉族姑娘缠足的动作;元代,从宫廷舞蹈变成现实的汉族民间小脚舞蹈的足迹。到明清时代,这种小脚舞蹈走进疯狂的民间,走入南方的乡村。
但我们无法知道缠足起源于哪一天?哪一分钟?哪一个人?哪一个地点?
这个源头,像一张脆薄的土纸,一戳就破。
而它的过程,像条河;从宫廷到民间,从城市到乡村,从上流社会到普通百姓。我们看到事实的波浪,水流的浑浊,淹没的人群,呼救的声音。
这条河逐渐成为时间的地下河,变窄、变黑、变死。
它干涸的那一天,是一个节日,一个完美无缺的节日,标志着不同寻常事物的降临:天足时代的到来。
但是古怪的六一村,虽然距县城仅三公里,她们本该全部奔走到县城,沉浸到那个平凡的世界中,纯粹的生活中去,喊口号,挥旗子,放鞭炮,唱战歌,让小脚和灵魂得到放纵和开拓。但是面对节日,六一村的许多女人却躲进荒园、小楼或黑房中,继续做着男人耕田种地、赶马经商,女人生儿育女、纺线织布的幽梦。
她们在那个难醒的幽梦中,那个客观上保护着她们幽梦的城堡里,继续进行着荒诞不经的行为:为自己、为女儿、为孙女缠足,偷偷摸摸,处乱不惊、不动声色地收藏着她们的秘密:超现实地塑造着纤纤玉足。
我(作者杨杨)母亲、肖秀香、皮桂珍和李翠芬都是在“天足运动”呼声最高的时候,开始偷偷缠足;在小脚已经成为丑脚,缠足已经成为陋习的现实里,她们向历史伸出了挑战似的小脚:银莲或者铁莲(没有达到三寸金莲的审美规范的脚)。
我曾经精确地推算过十几位老人的缠足里程,如我母亲周秀英,现年62岁,于1946年缠足,1952年放足;现年65岁的皮桂珍于1943年缠足,1956年放足;现年63岁的李翠芬于1943年缠足,1950年解缠,1951年再缠,1958年放足。她们三人都是典型的“解放脚”。其他如现年70岁左右的小脚女人,也是在共和国成立前后,缠缠放放,放放缠缠,一同被称为“解放脚”。那些现年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也曾放过,但是终因无法复原,只好缠至如今。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