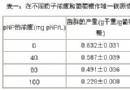精神生态和消费性审美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文艺总体上在走向世俗化,不仅通俗文艺充溢社会的各个角落,就是精英文艺也在市场经济的强大压力下逐渐退缩,流向世俗。有意味的是,作为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文艺学和美学,也部分地迎合着这一趋势,由形而上的研究转向了形而下的研究,北京的一些学者近来所谈论的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生活化,就是一例。美和审美,这个为哲学家和美学家研究了数千年的问题,现在已经简化为平头百姓日常生活的口头语:“好看”和“好听”。这是否真的印证了“真理是朴素的”这一至理名言,还是“越高贵者越愚蠢,越卑贱者越聪明”?
“美”是什么?在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探讨过,对它所作的解释不胜枚举。我们只要翻阅一下柏拉图的《大希庇阿斯篇》、狄德罗的《关于美的根源及其本质的探讨》和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就会发现这三位大师所搜集的有关美的定义,多得难以数计。我才疏学浅,没有对此仔细研究,但据我所知的近代以来的一些美学大师,尽管定义不同,却都把美圈定在形而上的精神领域,审美是一种充满诗意的、具有理想信仰品格的精神活动,它和粗陋的实用占有欲望无关。自然,这是前人所述,今人未必要死守此种信条,人们往往容易从已有的观念出发来评价事物,这并不符合历史主义原则。人对已知世界的了解现在还只能说是未知世界冰山之一角,美与审美大致也是如此。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随着思想观念的不断改变,人们从精神的审美要求走向物质的审美要求,走向日常生活的审美要求,实无可厚非,例如,让自己的肤色更美白一点,让自己穿得更漂亮一点,让居室更雅致一点,总之,让耳目所及都更宜人一点。所有这些,我认为是人所追求的正常的审美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我还是很赞同“生活审美化”的提法。
但是,问题在于,用精神生态的标准来衡量,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有根本性的缺陷的。日常生活的审美活动在现代社会里是属于消费性的审美,它和诗意性的审美相去甚远。前者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之上,后者诉求的是精神;前者和人的实用占有欲望相连,后者徜徉于理想化的超然境界之中。正因为消费性的审美和物质,和实用占有欲望贴近,这种审美活动带给人们的只是一时的快感,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必是无尽的精神紧张和压抑。一个无可否定的逻辑是,消费的前提是拥有金钱,金钱的获得是付出劳动。付出的劳动越多,获得的金钱才越多,消费性的审美活动也才越有可能。在这个逻辑圆圈当中,要命的是这种付出的劳动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被迫的,是异化的,这种被迫的、异化的劳动使人的体力和精力将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折磨和摧残,精神面貌会处于长时间的紧张之中。审美活动本来应该是自由的,是心情放松的,是精神生态的,现在却和不自由、紧张、精神恶化结合在一起。想一想一身高档的时装需要花去多少辛劳才能获得这一种消费性的审美,其间被掩盖了的精神苦痛不言而喻。这就是消费性审美活动的本质,也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真正内在涵义。因此,就我的认识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因为有悖于精神生态,它不应是人类追求的真正的审美活动。
然而,我们讨论问题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离开现实侈谈审美,总有瞎掰之嫌。在中国目前大多数人在为温饱或者为小康生活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在世俗化生活方式风靡整个社会的今天,和物质享受密不可分的消费性审美毕竟处在人们追求的审美活动的第一位。物质决定精神,这个有点古老的箴言并不过时。想当初,陶渊明如果没有较为舒适的生活条件,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会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然审美心态。今年2月,北京人大会议期间,时任代市长的王歧山听着代表的发言面临着一个议题的两难:住在破旧居屋里的市民强烈要求拆迁,希望能够搬进新楼;已经有了现代居室的市民则要求保留北京的传统街貌,认为那是文化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老胡同、四合院具有非常的文化气息,也有着无穷的审美价值,但是,对于那些住在那里还没有舒适便利生活条件的人们来说,是不会有那种纯粹属于精神性的诗意审美的。他们当务之急要求的是新型的漂亮的住宅小区里的那种生活环境,那种属于日常生活的审美环境。由此看来,恐怕要经过一个历史的轮回,社会整体性的审美活动趋势才会由现在的从精神的审美要求走向物质的审美要求再回归到精神的审美要求,诗意性的审美尚在未来。(这里强调,我说的是社会整体性审美趋势,而不是指单个的审美现象)
|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