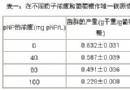“天人合一”与中国传统的生态意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源远流长。先民们从对自然的敬畏到与大自然产生亲和关系,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中国人对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的体验,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很独特的。史前时代稻米作物的种植,虽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环境对人的生存压力推动的,但由攫取性的生存方式向生产性的生存方式的过渡,反映了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日渐觉醒。在农耕为主的生产背景中,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对风调雨顺的期盼,使得先民们在对四时交替、气候变换格外敏感,逐渐形成了与环境和宇宙间的自然生命相互依存的文化心态,认为人的自然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是协调、统一的,反映了人们在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亲密的关系,即“天人合一”的心态。
天人合一在人与自然亲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关的文化心理,这是人以诗意的情怀去体悟自然的结果,认为人与自然本为一体,是一种亲和关系。自然万物是愉情悦性的对象,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身心的愉悦。在审美活动中,个体投身到自然大化中去,实现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的融合。人参天地化育,反映了人对自然的积极回应与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中国美学正是从“天人合一”的生命情调中,即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中寻求美。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正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在审美的层面上,人既不是自然的主宰,也不是自然的奴隶,而是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是天人和谐境界。
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和荀子就主张人体天道,尊重自然规律,对林木水产的捕伐要依时令而行。孟子主张“斧斤以时入山林”,荀子主张“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万物以时而生,时是生命生存的重要条件,生不逢时,就会缺乏生机,乃至走向死亡。《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吕氏春秋•审时》也多次强调要“得时”,要“不违农时”。《礼记•月令》则非常详细地讲了春夏之际,严禁滥砍滥伐,和保护孕兽,有助于树木的生长和鸟兽的繁衍。《礼记•王制》更是反对暴殄天物。
儒家突出地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善和谐。孟子提出了尽心知性以知天,“万物皆备于我”,将自己的情性与万物的本性相联系,讲求“物我同一”。到宋代,张载更是提出了著名的“民胞物与”的命题:“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以天地之体为身体,以天地之性为本性。将民众看成是同胞,万物看成是朋友。这些都是站在人为中心的立场上强调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与保护。这种生态环境既是物质的环境,也是精神的生态。
道家则向往回归自然,庄子追求“以天合天”,人与物为一,通过遵循自然规律的方法以求得精神的自由。“人与天,一也”;“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庄子•山木》)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天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庄子•齐物论》也把人看作大自然的一部分,与大自然本为一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要求人的行为都应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统一——“与麋鹿共处”。
在充满诗情画意的中国文化历程中,历代的文人骚客都在他们的诗文中传达着他们对天人合一的真谛的体悟。程颐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表现了诗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怡然自得的心态。王维在他那 “明月松间照”、“人闲桂花落”一类的山水诗中表、传达了人景相依的情怀。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也在物我为一的感受中提升着自己的心灵境界。
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仅影响到各意识形态领域,而且还影响到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国家。韩国的“身土不二”观念,就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展开。“身土不二”是韩国医学家许浚在1610年完成的医学名著《东医宝鉴》提出的。它的意思是:人身和土是不能分离的,人生活在土地上,食用土地上长出的东西,如果适应环境,就会身体健康。“身土不二”说明了人和环境互相依托的辩证关系,当环境遭受破坏以后,人类自身也会受到影响。上个世纪60年代,韩国民间组织“韩国农协”把它作为口号,号召国民消费本国的农产品,意为“韩国土地上生产的东西最适合韩国人的体质”,韩国人应该吃韩国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当然,他们推而广之,在对待其他商品上也要求做到“身土不二”,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而韩国人“身土不二”的观念中更为重视的是保护有限的生态资源。
在现代社会不断前进的滚滚车轮声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日渐隔膜,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的精神状态也自然地受到了影响,生态危机已触目惊心。在此背景下,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光辉思想,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