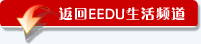农夫市集是一种“替代性食物流通体系”(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它注定了不能服务大多数人,不能成为社会主流。但从长远看,它还是能解决一部分人的生计问题,和另一部分人的信仰问题。这两样加起来,便是一个民间自建的“食物共同体”。“你必须承认,现如今中国的社会也有这样的需求。”常天乐说,“除非你选择对地沟油和假鸡蛋视而不见。确实是有一部分人,他们试图从大超市和国营菜场以外寻找对食物所产生的安全感。”
2011年4月,常天乐为北京农夫市集注册了微博账号,她觉得这种方式更利于市集与本地消费者进行实时沟通。“那时候,我觉得农夫市集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社会实验,我很想知道一个具有社会价值的东西能在多大程度上自发地在社会空间内成长。通过微博,我也想知道普通老百姓可以把这个事情推动到何种程度。”她在微博上发布很多关于市集的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谁谁在市集上买了新鲜蔬菜,回家炒成了特别漂亮的一盘菜的照片;又比如市集上的“微服私访”,一位跟农户攀谈的小个子台湾女士,其实是正好路过北京出差的著名美食作家韩良忆。
微博的影响力让北京农夫市集名声大噪。到2011年6月,几乎每次市集都人头攒动,并且来的大多数是本地客人,还有许多人在微博上留言,“想成为北京农夫市集的志愿者”。这让常天乐觉得很有成就感。而与此同时,作为市集最早发起人的绘美和迈克尔慢慢淡出了,但他们还是会参与一些有关的艺术项目,比如设计市集海报之类。“但遇到一些深层次问题,我还是会去找他们多聊聊。”现如今负责了大部分市集日常事务的常天乐说,“在北京农夫市集上,老外的志愿者与本地志愿者的区别在于:老外更关心农夫市集骨子里的‘精神’,他们比较理想主义,比较文艺青年,比较不看重利益。而本地志愿者,他们聪明、机灵、直接、简单,干活很麻利,做事很务实,但同时我也不得不说,其中一些人,他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市集可以带来的一些利益。”为此,常天乐精心地筛选市集的全职工作人员。“必须是有热情,有能力,并且不是那么看重利益的。”她无奈地说,“短时间内,市集没办法发出工资来。”
现阶段北京农夫市集的全职工作人员不超过5个。总是在市集上跑前跑后协调各种关系的齐大福,本是公司做行政的普通白领,她最早就因为在市集上买到了一只肥美的鸡,回家炖汤后觉得味道非凡的美,这才成了市集的志愿者,后来因为老跷班跑来帮忙,就干脆辞职全身心投入了市集。而原本在公益组织工作的马小超则是市集最年轻的工作人员,她曾经在农村工作过,是市集中少有的真正有下乡经验的成员。俞露则是市集“小厨房”的负责人,她曾经在加拿大生活,后来嫁到北京,最早也是市集的顾客,只不过这位顾客很擅长做菜,每次买了市集的食物,都会第一时间做成美美的菜发在自己的微博上。作为消费者代表,她也特别积极地骑个自行车跑来开过几次市集工作会议,顺道给大家带点自己做的小饼干什么的。“小厨房”的概念来源于某次市集需要500块钱的场地租金,常天乐坚持说,不能让农户出钱,这样不太合理,但农户们又坚持要为市集场地出自己一份力。最后结果是,农户们自发捐了些食材,由俞露把它们做成了三明治、汤、沙拉、豆浆,在市集上直接售卖,结果这一块的收入相当好。常天乐由此想起了自己在纽约农夫市集上的“完美购物体验”,提议大家把这个项目保留下来,就让俞露来主理“小厨房”。这个项目的意义有二,一是从侧面告诉来市集的顾客们,本地食材也能做出非常好吃的东西;二则是用来为市集本身筹经费。现在,只要是场地条件允许,“小厨房”在农夫市集上都会格外抢眼,因为它主要卖一些在普通超市里比较难买到的手工食物:猪油、罗勒酱、茶叶蛋什么的,夏天有酸梅汤,秋天则有鲜肉月饼,大家在市集上看到了新鲜出炉的食物,都兴致勃勃地踊跃购买。而每一次,“小厨房”也都会把制作这些食物的配方向顾客们公开,以公示这是没有其他添加物的纯“自家制”产品。
北京农夫市集自去年8月走上正轨以来,每星期办一次活动,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市集的消费者,除了最初那些纯粹寻找“别样购物体验”的年轻人之外,更多的中高消费人群进入市集,成为中坚的消费力量。“一开始很多小青年觉得农夫市集是在大城市里每逢周末的赶集,是一种全新的买东西方式,跟玩儿似的。但可能他们买的菜就那么一两样,并且由于太过年轻的城市人,他们根本很少在家里开伙,所以买菜只是一种新奇的尝试,很难持久。但后来,那些带着孩子的夫妇和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在农夫市集上出现得越来越多,比例也越来越大,我觉得这群人才是农夫市集最稳定的客户。”常天乐说,这样的顾客不再像那些年轻顾客,总是追着农户问“怎么会想到去种地的”之类的问题,他们更认真地比较各种产品之间的差别,追问农户作业的方式,想知道农夫市集以何种手段来把关农户和产品的质量。“这些顾客是较真的,是苛刻的,但我也非常清楚,如果农夫市集给了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他们将在很长时间内追随市集。”
农夫市集如何对自己平台上的农户及他们的农产品把关,这是农夫市集产生至今争议最大的问题。国外各类农夫市集依靠的大致是考察与诚信结合的“愿打愿挨”体系:其工作人员会对入场的农户做一些基础的考察,如农场的规模、产品的质量,以及是否按照承诺的方式种植等。但假设农户真的想在某一环节偷工减料,所谓的认证系统是很难发现的。“诚信是农夫市集最重要的基础,消费者在农夫市集上与食品的生产者面对面,听他们讲述,品尝他们的食物,从彼此陌生变成相熟的老朋友。在一段彼此信任的友谊中,朋友会带来更多的朋友。而如果这种信任因为一次作假受到了质疑,那你不仅会失去客户,还会失去朋友。”我曾经走访过的几个农夫市集,如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农夫市集,美国洛杉矶农夫市集等,在这样的市集上,一家小农户所开设的摊位,最大供应量平均是100个到150个客户,基本是你可以认识和记住的朋友数目的最大值,这种本地小农与消费者直接连接的供销模式建立起一个类似亲朋好友的圈子。而建立在这种诚信系统上的农夫市集并不比建立在认证系统上的更脆弱。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