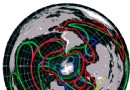毛乌素沙漠“黄”与“绿”的对决
它曾埋葬城池,驱赶牧人;而今却被牢牢困住,动弹不得。一千多年的骚扰告终,曾在陕西靖边县逞凶的毛乌素沙漠,正向鄂尔多斯高原它的老家溃退。翻天逆转,只用了半个世纪。然而,沙漠引退之时,干旱之魔又悄然降临……
逼沙丘北去
千年来,战争和超载放牧让鄂尔多斯高原不堪其苦,沙漠趁机向南扩张。明代陕北修建长城时,塞外尚草木森森;十八世纪初,长城已经被流沙裹挟。塞内十里的榆林,一度沙与城齐。包括靖边在内的榆林北六县,历年饱受沙暴之苦。
47岁的靖边林业局副局长刘玉军还记得上小学时,大风一旦刮起,就昏天黑地,教室里必须点灯。1984年,在林场工作的刘玉军正走着路,沙暴突然袭来,他和同事不辨南北,只好抱住一棵树等候,过后惊觉悬崖近在咫尺。
那些年,刚刚出苗的庄稼,常被春天的狂风连根拔起,或被飞砂打伤,农民因此被迫补种。运气不好时,一年要补种三四次。在极端的情况下,风力会搬来整座沙丘,覆盖了耕地。即使没有沙暴,流沙丘也会波浪状推进,蚕食绿地,平均每年前侵125米。农民们被迫一退再退。灰漠漠的靖边一度是国家级的贫困县。沙害不除,靖边人看不到希望。
“为甚治沙?被沙苦害了么。”88岁的郭成旺用黝黑变形的手指捻起一缕细沙。这位老护林员立在高地上北望,他家的绿地一直延伸到内蒙古。郭老1984年承包4.5万亩的沙丘植树治沙。如今他的地界上,已不见赤裸的沙坡,棵棵白杨下,是高矮不一的沙柳、花棒、沙蒿和柠条。这些草木,是郭成旺率领全家人亲手栽下。紧邻着郭老的承包地,还有全国治沙模范牛玉琴的绿地。治沙逾万亩的先进个人,在靖边县有好几位。
治沙不是80年代才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治沙始终是靖边的头等大事。
想稳住流沙,就得让植物扎根。1950年代起,农民们被公社组织起来,在沙丘下插植沙柳,在荒地上种树。这是靖边人有目的治沙的开始。
1984年,靖边农民听说出台了新政策:谁治理,荒沙地就给谁承包。一些怀抱雄心的农民,从此成为了治沙的主角。他们二十几年如一日地在沙里操劳,甚至把家安在了林地旁,林草因此大片成活。
80年代起,国家开始用飞机播种,把柠条、花棒等沙生植物的种子撒进沙漠腹地。沙障也派上了用场。沙障一般是用秸秆做的网格,置于沙丘谷底,飞播下的种子被风吹落于沙障,雨后整排长出,形成一道低矮的绿墙。随着沙地染绿,飞沙走石的现象逐渐消失,90年代后沙暴基本不再袭扰靖边。
2000年实行的禁牧令,巩固了治沙的成果。羊是靖边主要的肉食来源,也是绿地退化的罪魁。据郭成旺老人说:羊不仅吃植物嫩叶,还会啃树皮,刨草根,走过的道路寸草不生。政府封山,令行禁止。重罚之下,以往满山寻食的羊群,都关进了圈。
数十年的国家投入,郭成旺等治沙英雄的奉献,逆转了局面,如今是“人进沙退”。靖边曾有220万亩流沙,今天只剩下5万亩。沙丘削平,地表硬化,沙生植物的根牢牢扎下。坐在自己种的白杨下,郭成旺笑得舒心:“说治不住。不是治住了么?”
锦绣新垦区
高速公路穿过靖边沙地,路边一马平川,绿意不绝,极少见黄沙裸露。正是太阳最灿烂的时节,流云变换形状,阴影飘过空旷的草地,只有一两头骡子悠闲打盹。和传统农业区相比,靖边地广人稀。这里的农田十分年轻,不是改造自沙丘,就是改造自草场。
著名的无定河流过靖边,河滩地宽达一两里,很多就是“引水拉沙”造出来的。人们在沙丘底部挖出引水道,抽河水到高处,用水力拉平沙丘。河边农民施用此法已40年。获得的水田,可以用来种稻,甚至养鱼。
近年来流行用推土机造田。推平沙丘后,撒上厚厚一层黄土,施以有机肥,就可以播种。移沙化田,靖边称得上全国第一。
草场变身耕地的历史则伴随着教训。晚清人口膨胀,贫困的汉民从东方的黄土塬里迁来,向蒙古人买地或租地耕种,很快就把牧区变成了农区。他们种植玉米和土豆,也放羊,人口增加很快。为了烧柴和盖房,他们刨挖沙生植物,砍伐周遭的天然林,并很快尝到了苦果——风沙让他们的收成大大降低。甚至一年种下去多少,收上来多少。
今天,人们早已懂得了维护自然生态的重要。遵循退耕还林的战略,许多农田已经弃耕。按政策,如果把耕地转为林用地,农民可得到每亩每年将近两百元的补助。另外,卖一棵成年白杨的收益,顶得上一头羊。
若转种牧草,比如苜蓿,不仅能够给牲口提供青饲料,还可以肥田。不缺田种的靖边农民们,欣然改换了农业模式。
东坑镇是一片典型的新垦区。这里距离沙区20里,农户夯土筑墙,院落相隔很远。沥青道路横平竖直,交错出方正的交通网格。路边耸立着两排新疆杨。地里种植最多的是玉米,幼苗尚未过膝。沙质的土壤也适合土豆生长。农田旁有成片开紫花的苜蓿。林地里的樟子松还不到小孩高。除了山羊和绵羊,还有圈养奶牛的。听说为了农民增收,县里正在推广种植特种蔬菜,比如辣椒和芦笋。路边已能看到不少大棚。很显然,这是一块不愁温饱的土地。
在乡间还有许多微笑的、泰然自若的脸,尽管黝黑粗糙,脸上露出一种赢得决定性胜利的满足。
旱魔正窥伺
但战斗没有结束。一个新的敌人,干旱,悄悄设下埋伏。
毛乌素曾是中国最为湿润的沙地。沙表下不多深就是湿沙。即使是荒漠化最为猖獗的日子,毛乌素的地下水也十分充沛。直到70年代,在靖边的平地上打井,掘不到十米就出水,水质清冽。丰富的水资源,是靖边农牧业的基础。
而现在,一口机井要保持稳定出水,得打五六十米深。人们用粗管抽水,沿沟渠漫灌。据当地人说,地下水位之所以快速下降,是因为缺少公共水利,农民各打机井抽水,无统一规划,浪费严重。政府在推广喷灌,但少有农户主动去用。
地下水下降,使得湿地逐渐消失。以前靖边有许多小湖泊,方言叫“海子”,如今几乎全部干涸。靖边城西,本有一个宽达十里的海子,而今长满了红柳。
随之而来的,是树木不断枯死和早衰,尤其是白杨。这几年,成排的白杨树被伐去,代之以更加耐旱的樟子松和侧柏。在郭成旺老人的地里,白杨树也有了枯枝。他希望能筹款在林地里打口机井,除此外无法缓解旱情。
如果地下水继续枯竭,不光是树木,连最为耐旱的沙生植物也会折损。
近几年,靖边县的降水大大减少,且大多数是无助林木生长的毛毛雨。从去年10月到今年6月,还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雨。是全球变暖的缘故吗?谁也说不清。
如果这种干旱继续,很可能在未来导致沙漠反扑。一种新技术带来的好处,也许抵不过它造成的损失。机井,在保证靖边农业丰产的同时,却威胁到了生态稳定。
但政府无法像禁止放牧那样禁止机井。农民不担心禁牧,事实上圈养的羊比放养时更多。圈养羊吃的是玉米秸秆——秸秆曾被用做燃料,自从改善了交通降低了煤价,乡间普遍建起沼气池后,秸秆就节省了下来。
相比之下,如果放弃机井和漫灌,就没法保证田里的收成。唯一的办法是政府提供补贴,帮助农民转移到节水农业上来。现在转移成本不会太高,因为大多数农户赚钱不多。越快改变,危险就越小。
先民被沙漠消灭,今人却能转败为胜,这是因为人类学会了约束自己,并且使用石化能源增强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如今人们更需要思考,怎样才能改善这种自我管理,而不至于滥用科技巨大的力量。(本报北京6月16日电)
|
延伸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