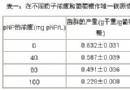生态主义话语:生态哲学与文学批评
这种公开的帝国主义宣言,集中体现了深层生态学热衷于荒野保护的多重危险。正如我所表明的,它大大加剧了美国运动忽视第三世界内部更为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倾向。但是,或许更重要、也更为阴险的是,它也为西方生物学家及其资助人、组织(如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帝国主义渴望提供动力。把一个在文化上植根于美国保护史的运动批发、移植到地球上其他地区,只能导致那里的人群在社会中背井离乡。[37]
古哈的批判或许有偏激之处,可是,他从生态“殖民地人民”的立场对深层生态学的普遍主义诉求及其政治后果所做的揭示,是值得深思的。生态主义者宣称不依附也不认同任何已有的政治意识形态,无论是左派(如社会主义)或右派(如保守主义)。在理论上,生态主义运动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然而,在实践上,尤其在全球范围的实践上,它能够保持这种政治纯洁性吗?从深层生态主义者对环境公正运动的谴责可以看出,生态主义对左派的态度是充满敌意的,毫不留情的;两个运动的实际关切与行动结果也大相径庭。但是,对于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右派,生态主义又如何表现呢?
我们以哈丁(GarretHardin)的“救生艇伦理”为例。“救生艇”隐喻说的是,世界好比海洋,富国好比海洋中的一艘艘救生艇,四周水面上浮满了穷人,随时有淹死的危险。“救生艇伦理”的核心问题是:在此种情形下,救生艇上的乘客该如何做?哈丁说,必须承认每艘救生艇的承载力都是有限的。以美国这艘救生艇而言,它现在承载着50人,慷慨点,假定其承载力为60人,即还可以搭乘10人(不过,这有悖“安全系数”原理),而在水中等待救助的有100人。这时,有三种可能:一是按基督教教导的“为他人负责”或按马克思教导的“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把所有人都拉上船。这样,船会因超载而沉没,每个人都被淹死——“完全的公正,完全的灾难。”二是既然这艘船还有10人的剩余承载力,我们不妨再搭上10个人。这样做会损害安全系数,我们或早或迟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更重要的是,选择哪10个人呢?是按“先来后到”,还是挑最好的或最需要的?我们如何来区分?我们又如何向被排除在外的90人交代呢?三是不许人上船,保持微小的安全系数。这样,救生艇上的人才可能存活,“尽管我们将不得不提防扒船的人群”。哈丁知道,许多人反感第三种解决方式,认为是不公正的。他承认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有人说“我为我的幸运感到有罪”,那么回答很简单:下去,把你的位子让出来。这种无私的行为也许满足了有负罪感的人们的良知,却改变不了救生艇伦理。那个接受有负罪感的人让出的位子的人自己不会为突如其来的幸运感到有罪,否则他就不会爬上来。如此下去,良知将在救生艇上泯灭。因此,“救生艇伦理常在,不以一时恍惚而改变”[38]。
“救生艇伦理”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极端代表,其理论价值在于其鲜明性。哈丁没有用任何修辞来掩饰其右翼立场。对于“救生艇伦理”,可以想见,深层生态主义者是绝不会赞成的。因为:其一,哈丁的全部议论都以发达世界主导的政治、经济规则的合理性为前提,这是深层生态学坚决反对的;其二,哈丁关心的是人口与粮食之类问题,在深层生态学看来,这只是细枝末节,专注于此不可能解决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其三,哈丁要处理的是当代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深层生态学则要优先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如何使地球生态系统不受或少受人类活动破坏。然而,在全球范围的实践上,“救生艇伦理”与深层生态学之间的对立好像并不那么分明。深层生态学极力推动的第三世界荒野保护固然保留了荒野,实际上却是对自然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结果,一方面富人的休闲、娱乐需要得到了满足,另一方面穷人的生存环境却没有得到改善(如果不是恶化的话)。从左派(如环境公正运动)的立场看,这种结果是无法容忍的,因为它加剧了环境不公正;从右派(如“救生艇伦理”)的角度看,前一方面且不论,而后一方面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反过来,左派致力于消除不同人群间的环境歧视,深层生态学对此不感兴趣;而右派一旦按哈丁的伦理行事,大量落水人群将无处存身,其道德上的困难恰恰可以借助深层生态主义者的断语来化解:“人类生命和文化的繁荣与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不相矛盾。非人类生命的繁荣要求人口减少。”深层生态学与环境保护领域的右翼思想在实践(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实践)上的这种默契,是令人震惊的!尽管深层生态主义者在此一窘境面前说他们并不反对人本身,只是反对以人为中心,尽管他们说每个人的维生需要都必须得到满足,富人有义务节制消费,然而,只要他们抱着人(全人类)与自然(地球生态系统)这个对立公式不放,这些言辞只能减轻他们道德上的负疚感,而不可能改变其主张的逻辑后果。
生态主义或激进环境主义作为植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世界的意识形态,在多数民主社会中能够有效地履行它的边缘政治职能。在此意义上,它的激进性质可以理解为一种姿态或策略,其目的是迫使主流社会伦理话语的操持者放弃权力垄断寻求妥协。可是,生态主义者并不满足于有限的边缘政治地位,而是要求普遍主义的实践。当他们把明显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建构方案无条件地加于这个仍然充满着阶级、种族、国家区分(歧视)的世界时,面对被漠视、被损害的人群,他们原初的志向和许诺就变得十分苍白。生态主义由于社会角色变换而具有双重政治意向,这一点在理论上必须清醒对待。我们当然不会因此否定它在当代历史中的合理性,以及它实际上具有的批判意义。但是,在发达社会之外,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一厢情愿地为其“前瞻性”喝彩,是否足够明智?至于世界范围的生态主义运动向何处发展,能否在未来的发展中对不同利益群体的环境关怀进行综合,从而导向一种真正的全球性实践,任何断言都为时过早。
注释:
[1]平肖(1865—1946)是美国资源保护运动早期代表人物,曾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1901—1909)任总林务管,并于1905年组建美国林业局;缪尔(1838—1914)是美国自然保护运动领袖,塞拉俱乐部(SierraClub)的创始人。
[2]SeeJosephR.DesJardins,EnvironmentalEthics:AnIntroductiontoEnvironmentalPhilosophy(2ndedition),WadsworthPublishingCompany,1997,pp.39-41;andDavidPepper,ModernEnvironmentalism:AnIntroduction,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6,pp.219-221.
[3]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1页。
[4]SeeJosephR.DesJardins,EnvironmentalEthics:AnIntroductiontoEnvironmentalPhilosophy,p.39.
[5]参见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第412—415页。
[6]SeeArneNaess,“TheShallowandtheDeep,Long-RangeEcologicalMovement,”Inquiry16(Spring1973):95-100;andhis“TheDeepEcologicalMovement:SomePhilosophicalAspects,”PhilosophicalInquiry8(Fall1986):10-31.
[7]AndrewDobson,TheGreenPoliticsThoughts:AnIntroduction,London:UnwinHymanLtd.,1990,p.13,p.35.
[8]DavidPepper,ModernEnvironmentalism:AnIntroduction,p.329.
[9]LawrenceBuell,“EcocriticalInsurgency,”NewLiteraryHistory30(summer1999):699-712.
[10]SeeCheryllGlotfelty,“Introduction:LiteraryStudiesinanAgeofEnvironmentalCrisis,”in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s.),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p.xviii-xiv.
[11]刘放桐主编《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上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页。
[12]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4页。
[13]AlfredNorthWhitehead,ProcessandReality,London&NewYork:HarperandRow,1960,pp.34-35.
[14]AlfredNorthWhitehead,ProcessandReality,pp.27-28.
[15]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99页。
[16]AlfredNorthWhitehead,ProcessandReality,p.33.
[17]SeeDavidR.Griffin,“Whitehead’sDeeplyEcologicalWorldview,”inM.E.Tucky&J.A.Grim,Lewisburg(eds.),WorldviewsandEcology,Pa.:BucknellUniversityPress,1993,pp.190-206.Cf.DavidPepper,ModernEnvironmentalism:AnIntroduction,p.242.
[18]HaroldMorowitz,“BiologyasaCosmologicalScience,”MainCurrentsinModernThought28(1972):156.Cf.J.BairdCallicott,“TheMetaphysicalImplicationsofEcology,”EnvironmentalEthics8(Winter1986):301-316.
[19]SeeJosephR.DesJardins,EnvironmentalEthics,AnIntroductiontoEnvironmentalPhilosophy,p.207.
[20]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第313页。
[21]J.BairdCallicott,“TheMetaphysicalImplicationsofEcology.”
[22]参见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第395—396页。
[23]SeeDanaPhillips,“Ecocriticism,LiteraryTheory,andtheTruthofEcology,”NewLiteraryHistory30(Summer1999):577-602;中译文见王宁编《新文学史》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314页。
[24]ArneNaess,“TheDeepEcologicalMovement:SomePhilosophicalAspects,”PhilosophicalInquiry8(1986):10-31.
[25]详见拙文《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批判》(载《哲学门》第四卷第一册,湖北教育出版社1003年版),本节以下部分内容亦见于此文。
[26]ArneNaess,“TheDeepEcologicalMovement:SomePhilosophicalAspects.”
[27]ArneNaess,“TheDeepEcologicalMovement:SomePhilosophicalAspects.”
[28]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5—1496页。
[29]参见休谟《道德原理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7页。
[30]亚里士多德的说法(Justicerequirestreatingequalsequally),其现代表述是:正义要求同样对待人,除非他们具有基于正当理由不被同样对待的差别(Justicerequiresthatpeoplebetreatedequallyunlesstheyhavedifferencesthatwouldjustifyunequaltreatment)。此即所谓“形式正义原则”(SeeJosephR.DesJardins,EnvironmentalEthics:AnIntroductiontoEnvironmentalPhilosophy,p.227)。
[31]SeeJosephR.DesJardins,EnvironmentalEthics:AnIntroductiontoEnvironmentalPhilosophy,p.229;andMarkDowie,LosingGround:AmericanEnvironmentalismattheCloseoftheTwentiethCentury,TheMITPress,1995,p.143
[32]SeeJosephR.DesJardins,EnvironmentalEthics:AnIntroductiontoEnvironmentalPhilosophy,p.230.
[33]SeeCarlTalbot,“EnvironmentalJustice,”inEncyclopediaofAppliedEthics,Vol.2,1998,pp.93-105.
[34]TroyW.Hartley,“EnvironmentalJustice:AnEnvironmentalCivilRightsValueAcceptabletoAllWorldViews,”EnvironmentalEthics17(1995):277-289.
[35]SeeGeorgeSessions,“Introduction”toPartTwo,inEnvironmentalPhilosophy:FromAnimalRightstoRadicalEcology,pp.165-182.
[36]ArneNaess,“TheDeepEcologicalMovement:SomePhilosophicalAspects.”
[37]SeeRamachandraGuha,“RadicalEnvironmentalismandWildernessPreservation:AThirdWorldCritique,”Environ-mentalEthics11(Spring1989):71-83.
[38]SeeGarretHardin,“LivingonaLifeboat,”Bioscience24(1974):10.
文章录入:ahaoxie 责任编辑:ahaoxie
精彩图片
文章评论
数据载入中,请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