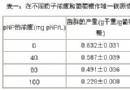苇岸:绿色文学的先行者
内容提要:文本结合文本分析解读了散文家苇岸的自然观与人生观,并提出苇岸能够以其宽厚博爱的胸怀去感受自然、接纳众生,并站在自然的立场上批判现代化进程中的弊病,因而具有深厚的生态哲学思想,他的写作是艺术性与生态性相结合的绿色文学的典范。
这是一颗充实的种子,但我怀疑他一直在阴郁里生长,虽然内心布着阳光。当他默默吐出第一支花萼,直至凋谢,都未曾引起人们的足够的关注。他的书,连同他一样是寂寞的。 ——林贤治
“我常常这样告诫自己,并且把它作为我生活的一个准则:只要你天性能够感受,只要你尚有一颗未因年龄增长而涡灭的承受启示的心,你就应当经常到大自然中去走走。”
39岁英年早逝的苇岸(1960-1999),也许是急于将自己的血肉完全地交付给大自然吧。看他诗般的语言哪一句不在表白他大地之子的身份!苇岸原名马建国,自幼生活在燕山脚下的昌平,在这个自然与文明的链接点上,苇岸一直保持着对大地的敏感和对文明的自觉反省。他的笔触和他的目光一道扫过了田野、山川以及草木、禽兽。
需要说明的是,说苇岸是绿色文学的先行者,并不意味着他是以文学为平台关心环境及人类出路问题的第一人。新时期文学在苇岸之前就有大量的环境文学问世,但环境文学的背后依旧是人与环境主客二分的理念,当人与自然被分隔开来时,自然作为客体必然与作为主体的人形成对立。环境文学作家们虽然意识到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但没有再进一步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在反思人的行为时仍然站在人的立场上,一切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认定自然是应当以作为人的资源而加以保护的。一言以蔽之,环境文学持有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其最基本的逻辑便是保护环境、动植物,是因为它们须更好地为人服务,而它们是否具有独立的价值甚至没能进入讨论的议题。这一思路的危险在于,当某些动植物,如狼、麻雀、野草等不具备经济价值时,就不在保护体系之内,甚至生存的权利都成为问题。王蒙在著名的环境文学杂志《绿叶》创刊号上所说的“人类终于结束了地球中心、人类中心、人类意志征服改造一切的一厢情愿的偏于幼稚的想法” 似乎为时尚早。
深受梭罗、利奥波德等人的自然思想和伦理观念影响的苇岸,其作品的风格不同于环境文学,而更接近在西方被称为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 的文体。一方面,他对博物学的重视反映了自然科学家的严谨。为了写作《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他居所附近的田野上选了一个固定的基点,每到一个节气都在这个位置,面对同一画面拍一张照片,形成一段笔记,时间严格定在上午9点,风雨无阻。另一方面,不论他的思维方式,对待自然的理念,还是对待人情世故,都体现了一种抛弃了二元对立,将个体置入整体系统的鲜明的生态性。因而他的作品,是真正的绿色文学。不过他的文字产量甚少。他生前出版了《大地上的事情》,在病榻上编了《太阳升起以后》,袁毅在他去世后有编辑了他的《上帝之子》。“他用一种季节轮回一样的速度,字斟句酌般缓慢地写作,他所有的文章不超过17万字。” 但文字的精美、和煦和深远却在他身后铺开了一条伸向野地——我们真正的家园的路。于是徜徉在他的字里行间时,我们不由自主地追随着他了。
1和谐之美:与自然共舞
生态学的整体主义观点认为大自然具有自己的运行节奏。所有的群落、社会的生息都遵循着某些庞大的、在自然中无处不在的节律。植物群落如森林、草原、灌木、植物结合体等只是气候及其他存在于自然中的或大或小的节律的生态产物。具有美感的自然写作是应该自觉地追求这种节律的。中国的生态批评家曾永成在他的《文艺的绿色之思》中提出审美形式是对富含生命节奏的自然世界的感应,而且能“激活生命节律感应以调节生命状态的动力。” 这是用中国的生态文艺学的话语对作者、文本、读者和世界的全新阐释,极具说服力地证明了文学的生态本质。好的作品不仅能够敏锐地感受自然界那鼓荡着的生命节律,还能通过审美形式把这种节律传递给美的接受者,从而起到沟通自然与人的作用。
文艺的生态性与美感成为同一种特质的不同表述,这在苇岸的写作中体现得十分完美。总的来看,苇岸对世界的感悟充满了和谐的精神,他对季节的敏感显示出他已把自己的生命节奏调谐得与自然完全合拍。如果节气是自然跳动的韵律,那么他踩着自然之舞的这些鼓点诠释了他对四季的体悟。梭罗的《瓦尔登湖》的最后几章,也显然跟从了季节流转的脚步。美国学者利奥•马克斯将这种对自然季节的认同视为对机械时间的抗拒:“这样的写法确定了把自身从时间中赎救出来的可能,肯定了摆脱钟表定义的康科德时间的举动,并迈向自然时间,即生命的季节性轮回。”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苇岸的节气写作受了梭罗的启发,但可以肯定的是,深受梭罗影响的这位中国作家,按照具有强烈的循环而非线性特点的阴历时间来临摹自然,必然与梭罗一样,是宁愿忘掉钟表的机械时间而遵从自然节律的。他在《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中用诗人的手仔细地把握着季节流转的脉搏,把人与野地的世界用相同的节拍贯通起来。比如他写立春:“带着冬天色泽和外观(仿佛冬季仍在延伸),就像一个刚刚投诚的士兵仍穿着旧部褪色的军装。”他写乍暖还寒的雨水时分:“土地隐没了,雪使正奔向春天和光明的事物,在回归的路上犹疑地停下了脚步。”写春分:“杨树现在则像一个赶着田野这架满载绿色马车的、鞭子上的红缨已褪色的老车夫。”他不仅自己享受着自然的节奏,也殷切地希望“弃绝于自然而进入‘数字化生存’的人们”能够想起古老而永恒的二十四节气。 他眼里的大地不是冰冷、被动的客体,而是活泼的、可以对话的。大量拟人和比喻的使用统一了自然的节律和我们生活的节律,只有把节气,把自然的风物当作生活中的是熟人,当作活生生的家庭的一员来看待,才会有此细致入微的体验和与自然界如此贴近的亲和。
苇岸的创作姿态本身也体现了他对市场节奏的抗拒和对自然节奏的遵从。他作品的产出稀少和精粹固然与他匆匆离世及思维的某种特性有关,但更是出诸他对艺术与自然的应和的理解。惟其如此,他才能感知现代人已觉察不到的野地里生命的充实。他的写作节奏已与自然的内在韵律同步,从而也能生发出与自然一样简约、生动的文字。选入《太阳升起以后》的游记散文《美丽的嘉荫》不仅使人感受到这个黑龙江小镇的宁静、美丽、温暖、祥和极其醇厚的家园氛围,还集中映照出作者对自然的深刻领悟。读一读第一段这恬静的语言:
“踏上嘉荫的土地,我便被它的天空和云震动了。这里仿佛是一个尚未启用的世界,我所置身的空间纯净、明澈、悠远,事物以初始的原色朗朗呈现。深邃的天穹笼罩在我的头顶,低垂的蓝色边缘一直弯向大地外面,我可以看到团团白云,像悠悠的牧群漫上坡地,在天地的尽头涌现。尽管北面的地平线与南面的地平线在视觉上是等距的,一种固有的意识仍然使我觉得,南方非常遥远,而北方就在我脚下这片地域。我的“北方”的观念无法越过江去,再向远处延伸,我感到我已经来到了陆地的某个端点。看着周围那些千姿百态的云团,每观察一个,都会使我想起某种动物,我甚至能够分辨出它们各自的四肢和面目。它们的神态虽然狰狞,但都温驯地匍匐在地平线上方,我注视了很久,从未见它们跑到天空的中央。它们就像一群从林中跑出饮水的野兽,静静地围着一口清澈的池塘。”
通过“我所置身的空间”、“北方就在我脚下这片地域”、“我注视了很久”等语句,苇岸意识到自己并非像站在风景之外的一般游客,而是全身心地融入进去。周围的世界不再是客体,而是与己交汇成一片的。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冷冷的观察视角,而是在四处游走之中用所有的器官及心灵去“看”。正因为如此,林贤治才会在比较苇岸和王小波时说:“王小波是科学的,苇岸是诗的。王小波用大脑思索,分割一切,判断一切;苇岸则用心灵承载,拥抱一切,感悟一切。 他的很久的“注视”是海德格尔顺应于事的“寻视(Umsicht)”,而不是“只对物做‘理论上的’观察的那种眼光” 。他用高贵而并不华丽的语言提醒我们去保留人类与自然交融的原初状态,使“事物以初始的原色朗朗呈现”,而不是在时空、精神上被人为地分割成碎块,因此在结尾部分他说:
“望着越江而过的一只鸟或一块云,我很自卑。我想得很远,我相信像人类的许多梦想在漫长的历史上逐渐实现那样,总有一天人类会共同拥有一个北方和南方,共同拥有一个东方和西方。那时人们走在大陆上,如同走在自己的院子里一样。”
屏除了财产观念而把美的事物呈给人们同等、和平地享有,这与爱默生的自然论有惊人的神合,后者在列举一片田产被数家人分割的情况后说道:
“但是他们中间的任何一家都无法拥有整个风景。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有着一桩财产——它不属于任何人,除非有人能以自己的目光将它所有的部分组合起来——此人必定是个诗人。”
没有艺术的眼光,怎能如此欣赏自然。只有像苇岸、爱默生这样把风景作为有机整体进行把握才能做到“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而由此还可得知,写自然的美文,其艺术价值竟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生态思想的注入。
2生态与生活:大地上的事情
大地上的事情》的篇幅薄得如同其作者瘦削的身材,但代表了他的温情、诗意和生态思想的集结。它由75篇类似散文诗的小短文串成,这些看似互不相干,仿佛从生活的长卷上随意剥下的片段,其实完全统摄于整体情境和隐藏在文字后面的主题思想——都是他对发生在大地上的事情的了悟,对最原初的风景的深情的一瞥和缅怀。对善良而微小的事物的关注,与之相应的温厚、亲切、不端任何架子的文体本身,以及让自然自己活动起来言说的叙述方式,已把人过去在自然面前的傲慢态度抹去,成为接受荒野和大地的前理解。
平心而论,苇岸的博物学知识不算专业,比不上梭罗、缪尔、利奥波德等美国生态文学家。不过他在观察自然物时所带的真诚与欣赏,是又比科学家的那种锐利的眼神高出一个境界的,因为他看蚂蚁、熊蜂、鹞子时的亲昵眼神表明他是沉浸在自然中去感受,而非居高临下冷眼旁观。或者说,他的眼光是一种另类的锐利。当他看到,在现代农业扫荡了往昔物种丰富的田野后,近几年又有喜鹊的巢星星点点地出现在树上,这使他感到欣喜。喜鹊以往一直选择高大的乔木筑巢,而今巢的高度已降低了。这不起眼的变化为他所捕捉时,就使他亮出了锐利的批评锋芒:
“鹊巢高度的降低,表明了喜鹊为了它们的生存而显现的勇气;同时,也意味着被电视等现代文明物品俘获的乡下孩子,对田野的疏离。”
一种鸟儿的家园的迁移在苇岸的注视下便投射出了自然在人的伤害下所表现的韧性,以及人因脱离了土壤而日益暴露出的脆弱。同一进程的两种表现,便通过普通的鹊巢得到了观照。下面不妨拿梭罗的一段文字来比较两者谱写的自然之歌的异曲同工。梭罗观察到初春时分,铺铁路基的细沙仿佛又重新听从了自然的驱使:
“自从铁路到处兴建以来,许多新近曝露在外的铁路路基都提供了这种合适的材料。……甚至还在冬天冰雪未溶将溶的时候呢,沙子就开始流下陡坡了,好像火山的熔岩,有时还穿透了积雪而流了出来,泛滥在以前没有见过沙子的地方。无数这样的小溪流,相互地叠起,交叉,展现出一种混合的产物,一半服从着流水的规律,一半又服从着植物的规律。……你望它们的时候,形态像一些苔藓的条裂的、有裂片的、叠盖的叶状体;或者,你会想到珊瑚,豹掌,或鸟爪,或人脑,或脏腑,或任何的分泌。这真是一种奇异的滋育……”
铁路和苇岸的“现代农业”一样代表了现代社会里无机的机械力量,当它们强行扭曲了自然原貌后,自然不屈不挠地恢复着自己的有机体,喜鹊的勇气和细沙的奇异图案正是这种进程的一个局部细节。因此,看似无甚关联的两段自然写作,实际上都显示了两作者对人的机械力量的暂时性和自然的独立演变的永恒性的领悟。比之苇岸的喜鹊,细沙这一切入点反映了梭罗更加富有想象力和诗意的洞察,接下去他得出结论:“世上没有一物是无机的。……你可以把你的金属熔化了,把它们铸成你能铸成的最美丽的形体来;可是不能像这大地的溶液所形成的图案那样使我兴奋。(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不过,无论是梭罗还是苇岸,他们所动用的意象都如利奥•马克斯所说,“是一种比喻,代表了被历史的机械化力量割断的(自然)形式与统一性的恢复。”
他笔下的麻雀“体态肥硕,羽毛蓬松,头缩进厚厚的脖颈里,就像冬天穿着羊皮袄的马车夫。”极富人情味的书写拉近了人与雀的距离,而后者“在树上就和孩子们在地上一样,它们的蹦跳就是孩子们的奔跑。而树木伸展的愿望,是给鸟儿送来一个个广场。” 这种对博物学明目张胆的诗性的违背,与中国美术的写意精神一样,是和那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借物喻人的散文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对科学的真实的变形是为了突出艺术的真实。作者在赋予麻雀孩子的性格时,并没有抹掉麻雀的身份,而是将之更明确地彰显出来——麻雀对欢乐的感受并不亚于人,当它获得了快乐的权利时,人也应该放弃迫害它的行为。西方的环境伦理学认为人以外的动物同样也是“生活的主体”(subject of a life),又体验生命,感知苦乐的能力,所以人去压迫、食用、使用它们都是反伦理的。苇岸就能充分感受动物们的生活体验,从而能够将其看成是平等的生活主体。不过在这里,与其说麻雀分享了人的高级情感,毋宁说它使人失去了优越性,于是麻雀-自然的身份便凸现出来:并非雀儿有许多人的特点,而是和人同享着自然赋予的灵性。平等是爱的前提,当人走下神坛平视世界时,才能去爱世界并获得世界的爱。先进的生态观必然是民主的,统治的逻辑在此也遭到逼视。所以苇岸在一个被毁的蜂巢前质问道:
“那个一把火烧掉蜂巢的人,你为什么要捣毁一个无辜的家呢?显然你只是想借此显示些什么,因为你是男人。”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生态女性主义指出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把荒野看成展示阳刚气概的地方,看成发泄好斗、探险甚或暴力冲动的地方。” 人类对自然的暴虐行径和男人对女人的耀武扬威被并置起来,若是我们渐已认识到男女平等的价值,那么人对自然的征伐也就失去了逻辑的基础。生态女性主义正是自觉地联合了这两股力量而成为文学批评的一支生力军,苇岸的以上思考则完全充当了该批评的注脚。
在《大地上的事情》中也有几篇写人和人的劳动的。苇岸相信人及人事都应该是属于大地,而使他特别感到亲切的是那些与大地贴得特别近的人及人事:儿童,农人,母爱,种庄稼。与之相应的是,他对束缚孩童的自由生长的所谓文明教化表示了明确的反感。他那略带哀愁的语言就像痛惜人的童年和文明的童年失去纯真的悼诗:“成人世界是一条浊浪滚滚的大河,每个孩子都是一支欢乐地向它奔去的清澈的小溪。孩子们的悲哀是:仿佛他们在世上的惟一出路,便是未来的同流合污。”他从背离光明的“北上”和接近光明的“南下”悟出,这就“像世间称做官为上,还民为下一样。”平民与草根意识浸润在他的文字和笔调之中。事实上,这种平和的心境不仅成为融入自然的先决条件,在苇岸看来,也是做一个本真的人的基本要求,如此,他对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认识便达到了统一。张炜在《融入野地》里曾说过,人若丢弃了劳动就会陷于蒙昧。和他一样,苇岸也重视劳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媒介作用,因为土地“叫任何劳动都不落空,他让所有的劳动者都能看到成果,它用纯正的农民暗示我们:土地最宜养育勤劳、厚道、朴实、所求有度的人。”他提倡不管什么人,在一周中至少在土地上劳动一天,因为“它使我们自己与泥土和大自然发生基本的关系。”若非如此,自然万物就被隔断了来上手的途径。因而苇岸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一生从未踏上土地。” 也正因为如此,苇岸也特别欣赏“对劳苦农民给予深刻同情和关爱的” 张炜,而苇岸和张炜都热情地耕耘在自然写作的沃土上,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农民的兄弟吧。
《大地上的事情》中的第39节是为数不多的生态思想的直接表达。苇岸从独特的发生学的角度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史:
“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很像人与他的生命的关系。在无知无觉的年纪,他眼里的生命是一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井,可以任意汲取和享用。当他有一天觉悟,突然感到生命的短暂和有限时,他发现,他生命中许多宝贵的东西已被挥霍一空。面对未来,他开始痛悔和恐惧,开始锻炼和保健。”
苇岸的比喻告诉我们这样几层意思:首先,人与大地之不可分割,就如同人与自己的生命一般,对自然的蹂躏便和糟蹋自己的身体一样愚蠢;第二,自然资源和生命一样是有限的,因而是珍贵的,人年轻时很少想到死亡,是出于对生命无限的错觉,人的文明在对待自然资源时有同样如此;第三,人对自然的认识,应该是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懂得害怕,是成熟的征兆,我们现在正开始“痛悔和恐惧”,这并非是一件坏事。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苇岸在面对未来时是乐观的,因为“人类并不是一个人,它不是具有一个头脑的整体。今天,各国对地球的掠夺,很大程度上已不仅仅为了满足自己国民的生活。”个体的自省,代替不了文明的觉醒,“理性”巨大的惯性力量比一个人的明知故犯要可怕的多。不过苇岸的写作活动本身,特别是第43节中他对科学祛魅的反感表明他并不放弃对重返自然的呼唤:作为强大征服者的科学“改变了事物自体的进程。科学的使命之一,就是统一天下事物的名称。它以一种近似符号的新名,取代了与事物有着血肉联系的原始名称。”给予他信心的是,“科学的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而各地的‘原生力量’,也从未放弃过抵抗”。 苇岸的希望
文章录入:ahaoxie 责任编辑:ahaoxie
|
延伸阅读
|
精彩图片
文章评论
数据载入中,请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