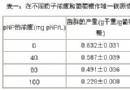藏族传统文化生态概说(四)
四、藏族传统游牧方式
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又要发展自己。为此,藏族传统的牧业活动与农牧业相结合的农业方式都非常注意保护环境,限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使经济活动保持同自然环境的协调。
藏族牧民的空间意识中,他们认为一个部落所处的地域是人、神和动物的共同居住区。因此,这块区域中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在神灵面前都是平等的。它们都源于同一种生命体,长期演化发展中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感应,互为因果,共生共存的密切关系。
人类畜牧活动的目的是,既要照看家畜又要保护水草,在此前提下获得有限生产生活资料,以维系自身的生存发展。所以牧民畜牧活动并没有积极介入自然生态系统,并没有加以主动开发和过分干预。在人与其他生物的关系中,既要维持人类自身的生存权利,同时又要与其他生物共同生存。至少不至于造成其他生物的灭亡和消失。这便产生了人对自身生产、消费的限制和对自然界的有限利用为特征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处理牲畜饲养与牧草生长关系中,牧民认定,所有生物都是平等的,都是与人共生的,相依相存的,因此就要兼顾各方利益均不受侵害;作为牧民,既要保护畜养动物,又不能使养育食草动物的基地——草原草地受到致命的损害。在动物之间的关系中,牧人既要畜养已驯化了的家畜——牛、马、羊等,但也要注意保护野生动物的生存权利。草原上的这些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有时会对牧民家畜生存造成威胁。比如,一个地方野生食草动物过多,就抢食了家畜牧草;狼也是家畜的危害者。但牧人认为这并不是经常发生的现象。当发生大雪灾时,高山野生动物就会下山抢食牧草;当草原野生食草动物急剧减少时,狼才会袭击家畜。对此只能通过调整系统内生态平衡来解决。于是产生了种种宗教仪式和经济活动规范。其中畜牧活动规范至关重要。
(一)畜牧类型与数量控制。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财富,即实现经济效益最佳化。利润是人们经济活动的最大动力。除此以外的非赢利性经济则被认为是非理性的。
按这种观点,畜牧业经济,自然是要饲养更多的家畜以获取更多的利益,使人发财致富。不过,在青藏高原的藏族畜牧业中,我们却发现了与现代经济学模式不完全一致的另一种方式,这便是对高原生态环境加以融合的畜牧方式。这种畜牧方式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通常有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放生”类型:饲养“放生”家畜是人与各类家畜共同生活在一起,人对家畜采取一种永久的照顾、看守的责任与义务,从而成为一种人畜同生的现象,也成为牧民的生活方式,牧民将自己家养的牛羊都看成“放生”的,将牲畜从生到老死一直在看护、照料,从不宰杀,也不出售,牧民在放牧过程中每年获取的牛羊毛、牛乳等产品供自己消费。同时“放生”牛羊的主人亦将牛毛、羊毛及自然死亡的牛羊皮及其乳制品驮到农业区,换取青稞炒熟磨成面粉,作为日常“楷粑”食用。
“放生”作为畜牧活动的中心和目的,这在藏区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只是“放生”的数量不同,有的牧人只放生自己畜群的1/10,有的放生1/3。也有人是象征性地放生一两只(头)。这里较为典型的是20世纪20~50年代西藏山南地区的“赤钦”,他是统管山南拉加里地区的王爷,辖区方圆3 500平方公里,具有独立的社会经济制度。历史上赤钦直接接受达赖喇嘛的指令,行动上不完全接受噶厦政府的支配。赤钦全名叫拉·朗杰加措,他管辖2 000余户农牧民,直接拥有7 000亩耕地、12个牧场;饲养牦牛近4 000头、绵羊2 800只。赤钦将饲养牛羊看做一种慈善事业。饲养数千头(只)牛羊是为了照料牛羊安全度过一生,因此,他的牛羊全部是“放生”的牛羊,既不向外出售,更不宰杀。只是让牛羊在他和他雇用的牧人照料下,成长、肥壮、自然老死。赤钦家族及其雇工每年的生活费用主要取自每年自然死亡的牛羊及皮毛畜产品。
其二、淘汰瘦弱体保护整体的类型。所谓保护整体,即牧民在放牧过程中,每年冬季初挑出一批老、弱、病、残的牛羊,及时出售或宰杀。这样做,从牧民心理看,认为这类牛羊在冬初不及时淘汰,那么来年春季牧草干枯,气候恶劣的情况下,就会冻饿死亡。从保护其他牲畜,保护草场出发,这种牺牲小量保存大量的策略,是让大部牲畜发展、草场受到保护的适宜策略。至少一个部落中多半的牧民在“放生”的同时亦采取这种方法。
其三、维持生存型,即牧人畜牧牛羊为了获取生活资料生存,同时也保护草畜生态平衡。但是满足牧民生存消费的需要,也仅仅维持在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之内,靠养畜来推动经济增长,积累更多财富的想法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二)家畜种类选择。
如果从经济效益计算,牧民大量饲养绵羊是最有价值、最有利可图的。藏绵羊生长繁殖快、食草量较少,其羊毛在国际市场上号称“西宁毛”而驰名,羊毛产量比牛毛要多,故能获大利。而牦牛繁殖少、生长慢、食草量大,牛毛产量很少,故从经济上看养牛是不划算的。但是,一个部落的经济、生态系统中,往往不是以羊为主。青海南部果洛地区牲畜结构比例中,绵羊与牦牛的比例为1:1.1,环青海湖地区为3:1。牧民将自己畜群中主要两大类家畜——牛与羊分为这样的比例,实际上有生态学、经济学与文化学方面的根据:
从地理学看,为了适应当地自然环境而进行选择,果洛地区海拔3 800~4 500米,牦牛高度适应这儿的高寒环境。环湖地区海拔高度略低于果洛地区,也在3 200米以上。牦牛耐寒冷,善爬高山,能食高寒地草,故自古以来一直繁衍生存。
从生态平衡的意义看,一个生态系统中,一定的生物都有互补、互助的功能,以维系生态平衡,所以一定的生物种类与数量保持相对稳定。牦牛生活于高寒地带,它可以利用夏季牧场最高最冷地方的牧草,亦可利用绵羊不能利用的湿生植被,同时采食牧草的高度较低。所以牦牛与绵羊的资源生态位置有错位,从而使一个地区的牧草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另外,牦牛可以到一般绵羊到不了的湿地、高寒地去觅草,它们的粪便可以为这地方的植被提供养料。同时,牦牛对高原寒冻、雪灾、大风等具有更强的抵御能力。牧民们认为,大量的牦牛与绵羊共同生存,绵羊生长似更容易、更健壮。而单独的绵羊群则成活率低。
从经济效益看,牧牛是保证牧民维护自给自足生活的主要来源。牧民的住所——帐篷原料全部来源于牦牛;牧民食物中主要成分肉、乳、酥油亦来自牦牛。牧民部分生活生产工具如绳、皮袋等来源于牛;牧民的燃料主要是牛粪。同时,牛又是草原主要交通工具,牧民靠牛驮运搬家。从文化角度看,在藏族民间牦牛尤其是白牦牛是以神的形象出现的,人们对牦牛保持着崇拜的信念。家有牦牛,给牧人精神生活带来丰富的内容。
牧人普遍有与其他动物同生同长的观念。自古以来,牦牛、藏绵羊生活于高寒高原。作为牧人,只是想维持这种自然选择的结果,并不想为谋利益而人为控制某种动物。所以我们看到每个部落、每个牧户中总是饲养绵羊、牦牛、马、狗及少量山羊共同存在的情景。
牦牛、藏羊、马、少量山羊及狗,是藏族牧人的主要饲养动物,这种选择,乃是对高寒自然生态环境适应的范例,只有牛羊马能利用广袤的草原,啃食绿色植物茎叶,而不会对其根部产生破坏。同时,它们的反刍功能能充分利用牧草。在牧区人们不会饲养猪,猪需要大量粮食饲料,如果开垦草地种植大量饲料,势必造成对草原的破坏。
(三)游牧方式。
游牧方式是一种较典型的既饲养家畜又保护草原的方式。古人称游牧为“逐水草而居”,实际上“逐”是循自然规律所动,按自然变化而行的行为。
当每年5月底到6月初,青藏高原海拔3000米以上草原地区进入暖季,气温在5℃以上,高寒山地草甸类、沼泽草甸类、灌丛草甸类草场青草已长出长齐,早晚气候凉爽,又无蚊蝇滋扰。牧民们此时进入高寒草地,喜凉怕热的高寒地带牲畜很适宜这种气候,又充分利用高山草原牧草资源。而冬季所居的大面积草场已完全无畜,使牧草能不受干扰地充分生长。同时,原先的草地以及食草动物、食肉动物等组成的生物链系统亦得以不受干扰地充分发育。
夏季的高寒草场,各种植物利用短暂的夏季迅速生长,牧民放牧一般是早出晚归,让牲畜充分利用生长极快的牧草,早晚放牧于高山沼泽草地或灌丛草地,中午天热时放牧于高山山顶上,或湖畔河边泉水处。此时大量的野生岩羊、黄羊与家畜遥遥相伴,甚至混群,情景非常可观,牧民们不会去干扰的。这个季节是牛羊发情交配的季节,也是剪羊毛的时候。
8月底9月初,高寒草场天气日冷,气温降至5℃以下,夜里一场大雪会把草场覆盖,不过中午又会融化。此时牧草停止生长,而变得枯黄。于是牧民又驱畜进入山地草场,也叫秋季草场。在利用了这段地区牧草资源后,10月下旬进入冬季草场,这里一般是海拔较低的平地或山沟,避风向阳,气候温和,牧草多系旱生多年生禾本科牧草,它返青迟,枯黄晚,性柔软。经过一个暖季的保护,已长20厘米~30厘米高,足够家畜在漫长的冬季食用,这时节放牧一般晚出早归:当太阳照得暖洋洋时才驱牛羊缓缓出圈,晚上太阳落山前即回畜圈。同时放牧先要选择草地:“先放远处,后放近处;先吃阴坡,后吃阳坡;先放平川,后放山洼。”这是放牧的经验。
牧民们总结出了利用不同草地,不同季节与气候放牧的经验,比如“夏季放山蚊蝇少,秋季放坡草籽饱,冬季放弯风雪小”。“冬不吃夏草,夏不吃冬草”——要充分保护不同季节的草场草原。“晴天无风放河滩,天冷风大放山弯。”“春天牲畜像病人,牧人是医生;夏天好像上战场,牧民是追兵;冬季牲畜像婴儿,牧人是母亲。”春天应精心照料牛羊;夏天尽量让牛羊吃饱;冬季则小心护养它们。
牧民放牧的藏羊有适应高原干旱、寒冷环境、耐寒怕热、喜干燥而怕潮湿的特性。藏羊能在-25℃左右的风雪中照样奔走于高山觅食,母羊仍在露天产羔,羔羊不会因寒冷而冻死。但是牧人无论阴晴雪风,无论寒冷干热,一年365天,都必须天天放牧,时时操心他的羊群。牧人跟着羊群转,羊群随着水草走,人畜都循一年四季天气变化而游牧。这种恒定的路线,不变的轨道,牧人无法突破,他守护和驾驭着羊群,但他又被自然所支配。他们世世代代承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成为自然规律被动的执行者、维护者。所以他们的畜牧生活几千年来几乎无太大的变化,20世纪40年代的游牧生产方式与吐蕃年代的游牧方式并无明显区别。大概所有的游牧民族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把游牧生活称之为“虽然存在但无生长”的停滞的文明。由于游牧民族需要在不同季节为畜群在荒凉草原上寻觅生活资料,他自己的生活与行为必须准确地按时间表行动,因而游牧民族变成了每年气候与植物生长周期的囚犯;游牧社会成为没有历史的社会。
(四)“羊要放生、狼也可怜”——家畜与野生动物共生存。
在藏族宗教中,无论是现世生活场景,还是来世生活场景,人与各种动物总是同居一处相互依存。同样,在一个部落游牧的地域内,牧人也将家畜与野生动物都视为该区域的生存成员,既要放牧家畜,但又不干扰野生动物。家畜与野生动物共生同长。
在许多情况下,家畜与野生动物在同一地区和平共处。牧人的家养牦牛常爬上高山与野牦牛混群,有时公野牦牛引诱家养母牦牛到处游走几天不归,但因为牧人知其活动路线,故不急于找回。由于不惊扰它们,野生动物基本固定生活于一个区域,牧人便能识别它们,与它们朝夕相处,发生大雪覆盖草地的时候,野生动物与家畜挤在一起共觅食物,牧人若有饲料则要喂养一切动物。在一个部落拥有的大片草场上,牧人除了放牧家畜外,同时要留出大片草地给野生食草动物。即使对于游牧区域的野生食肉动物,牧人也不会主动侵扰它们,许多野生动物在宗教中是崇敬和禁忌的对象,如虎、狮子(不过藏区并无狮子)、鸟类中的鹰等。遇见所敬畏、禁忌的动物,人们敬而远之;一般称呼中亦不直呼其名。如瞎熊,不叫熊,而叫做刨土者;雪豹称之为长尾巴、方头等。
藏族游牧方式是对自然环境的谨慎适应和合理利用。这种方式限制了家畜数量的增长,使其不超出草原牧草生产力的限度。牧人保护草原一切生物的生命权与生存权,既养家畜又保护野生动物;既要放牧又要保护水草资源,从而维护了高原生物的多样性。按季节、分地域进行游牧使草地得到轮休生养。而节俭节约的消费生活方式使自然资源得以保存和更新。为了对自然资源不造成破坏性的开发利用,游牧社会与外界建立贸易关系,以畜产品交换生活消费品作为维护畜牧生态系统运转的必要条件。总的说来,这种游牧方式是对高原环境的适应,而不是破坏和干扰。使千年来高原自然生态环境未受大的人为破坏。对青藏高原高寒牧区来说,游牧方式不仅过去,而且在目前仍然是最适宜的方式,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保持优良的民族传统文化。如果从全国或者从亚洲地区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协调来看,保护青藏高原自然生态环境,对东亚和全国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